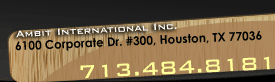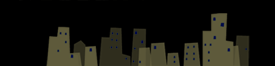我向來不喜歡塑膠花,無論它做得多真,我還是覺得假,而且因為以假亂真,愈發惹我討厭;但是自從六年前,聽陳清德說「那個故事」,我對塑膠花的印象就改變了,每次看見塑膠花,即使那種作得極粗拙的,也會由心底泛起一股暖流,想起逝去多年的陳清德。
雖然跟他不是深交,他又遠在馬來西亞,但是第一次在吉隆坡機場見到他,坐上他的車,就覺得跟他有默契。他跟我一樣容易「閃神」,是那種一邊開車一邊說話,一說話又忘了開車,到雙叉路口,突然大叫不好,該走左還是走右,然後幾乎撞上分隔島的人。
他說話有種特殊的語調,好像發抖又不是發抖,可能是氣不足,又急著講造成的;但細細聽,又因為他總是提著氣說話,用一種急切高亢的情緒來說,所以顯得有些激動。偏偏他說的不一定是激動的事,速度又不極快,甚至內容是娓娓道來,那急與徐、高亢與平淡之間就構成一種特殊的味道。
也可以這麼說,陳清德是個非常感性的人,不管多小的事,在他看來都可以很有感觸。舉個例子,他會去橡膠園裡撿橡膠子,然後拿來送我,說「你看,這多漂亮,咖啡色的種子,上面還有銀色花紋,好像是銅鑲銀的。」這還不夠,他會連那外面大大的果囊也撿來,一點一點剝開,露出裡面的種子,告訴我橡膠子的結構。
他也收集相思豆,有回裝了一小袋給我,說是特大的。相思豆我見過不少,但他拿來的果然特別大,而且特別紅。我說「好極了,我可以用它來作封面設計,可惜不夠多,我要很大一堆才成。」
隔不久,他就託人帶了一大包相思豆給我。我嚇一跳,也感動得要命,立刻用來拍成《對錯都是為了愛》的封面,又不知拿什麼回謝,想來想去,決定畫張畫給他。沒料到,在電話裡告訴他這個消息,他居然隔了半天,不吭氣,好像很猶豫的樣子。
「你不要?」我問。
「不是不要,是得要兩張,」他說,「因為我有一對雙生的女兒,將來結婚,如果只有一張,到底給誰?」我怔了一下,二話不說,畫了兩張寄去。
陳清德談到女兒,那語音就愈顫抖了,好像多年不見的女兒遠遠要撲進他懷裡似的。從他的言談中,我聽得出也見得出,他這麼多年的辛苦、節儉,都是為了這兩個寶貝女兒。
馬來西亞不是個很富裕的國家,黑黑瘦瘦的陳清德,半生致力推展華文教育,他身體不夠好,收入也不豐厚,卻拚全力,送兩個女兒出國念書。記得他去美國參加女兒畢業典禮回來,在電話裡對我說:「你們美國好美啊!尤其是蒲公英,滿地黃色的小花,在大大綠綠的草地上,太美了。怎麼我們馬來西亞都沒有蒲公英?」
「真的嗎?」我不信,「只怕是你沒注意吧。」
又隔一陣,他果然來信說發現大馬也有了蒲公英。我說:「不是有了,是早就有。只是以前你太忙、眼鏡度數又深,所以沒看見。到美國看女兒畢業,高興了,也有了輕鬆的心情,所以發現蒲公英。」
從蒲公英、橡膠果和相思豆可以知道,陳清德很愛植物花草,只是令我驚訝的,是有一回在餐廳,他居然盯著桌上插的塑膠玫瑰花,而且目不轉睛,一副十分陶醉的樣子。
「這花作得太粗了,」我說。
「是啊,一看就是假花,」他還緊盯著塑膠花,「可是這假裡有真哪。」
看我不懂,他笑笑:
「你知道嗎?現在這裡的年輕人也過西洋情人節了。」
我點點頭。
「去年情人節,有人一早就送了一大把玫瑰花來。女兒已經出門了,我看看上面的卡片,原來是小女兒男朋友送的。於是把那束花放進她房間裡,還拿個花瓶,裝了水,插著,」他作成捧花的樣子,「可是我一面把花放在小女兒床邊,一面看見大女兒的床,旁邊空空的,沒有男朋友送花,覺得好可憐,想她看到妹妹有人送花,一定會很傷心。」他看著我,扮了個鬼臉:「我當時靈機一動,想到櫃子裡好像存了三支塑膠的玫瑰花,是以前買生日蛋糕附贈的,就把花找出來,上面積了灰,我還洗洗乾淨,又從小女兒男朋友送的那把花裡切下一塊玻璃紙,把花包起來。正包呢,又想到,糟了!我還有個外甥女跟我同住,她也是大小姐了,也該有人送花,如果看見我兩個女兒都有花,就她沒有,更會傷心。就也拿一支塑膠花,包好,綁上絲帶。
於是,三個女生,每個人都在床邊擺了花,我正得意,看見桌子上還有一朵沒用的塑膠花,也還剩一小塊玻璃紙,那花雖然看起來最難看,好像掉了好幾個花瓣,但是何必浪費呢?我們家還有一個女人哪。」說到這兒,他又扮個鬼臉,一副老頑童的樣子:「於是我為我太太也作了這麼一支花,偷偷放在她的梳妝台上。」
「她喜歡嗎?」我試著問,心裡好奇極了。
「她沒說,」陳清德聳聳肩攤攤手,隔了兩秒鐘又一笑,「可是情人節過了,小女兒的鮮花凋了,扔進了垃圾桶;大女兒和外甥女的塑膠花也不見了,大概也扔了。可是,可是我太太的那支,雖然不怎麼樣,她卻還留著,而且拿個小瓶插著,放在梳妝台上,一直到今天,都在那兒。」他盯著餐桌上的塑膠花,用那顫顫的語調慢慢地說:「每次我看見太太坐在梳妝台前,旁邊插著那支塑膠花,都有一種好奇怪的感覺,心想『你為什麼不扔了呢?你為什麼不扔了呢?』」他突然不再說話,等了半天,深深吸口氣:「現在,我每次看見梳妝台上的花,都想哭,我發現跟她戀愛結婚幾十年,她都老了,我卻從來沒送過一朵花給她,那支塑膠花居然是我給她的第一朵花,她插在那兒,是給她自己一些安慰吧!或許……或許那雖然是朵假花,在她感覺,卻是一朵真花啊。」
講這故事不久,陳清德發現肝癌,又沒過多長時間,就永遠離開了。可是他說的這個故事,總浮上我的腦海,甚至每當我看見塑膠的玫瑰花時,就會想起他。
我常想,愛才是花的靈魂,一朵怎麼看都假的塑膠花,透過愛,就成為真花,而且永遠不凋。
我也常想,或許陳夫人的梳妝台前,現在還插著那支逝去丈夫送的 --無比真實的塑膠玫瑰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