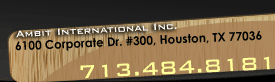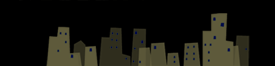廿年前我以開計程車維生,這種生活自由自在,不受老闆的約束,不過我倒沒想到那也可以服事他人呢!
我經常開夜班車,我的計程車無形中變成一個自白室,乘客爬進來後,坐在我後座,我們彼此從不打照面,他們覺得安全又自在,就很自然地和我聊起自己的一些事。
我接觸到形形色色的人,他們的生命有的令我驚嘆唏噓,有的令我肅然起敬,我也不禁和他們同憂同喜。
有一年夏天深夜,我所載的那位婦人的故事,最令人難忘。
那天深夜裡,我接到一個電話要我去鎮上一個安靜的社區裡一座小磚房接人。
我以為一定是去接參加派對,或一個與配偶爭吵而離家出走的人,或一個到工業區上夜班的人。
半夜兩點半,我到達時,整座樓都是漆黑的,只有一盞微弱的燈光從一樓的窗戶射出。
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司機只按一兩聲喇叭,再等一分鐘,然後就走掉了。
但是我知道很多貧寒的人,他們在緊急時,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計程車,所以除非感覺特別危險的地區,否則我都走到門前去。
我心裡想,這位乘客一定需要特別的幫助,於是我走到門前敲門,一個蒼老的聲音回答:「等一下」,我聽到好像在地板上拖拉重物的聲音,過了一會兒門開了。
出來的是一位矮小的老婦,她穿著一件碎花洋裝,戴一頂有紗網的無邊女帽,像四零年代電影裡看到的。
在她身旁是一個尼龍小箱子。
我探頭往裡看,那棟公寓像是長年沒人住的樣子,所有的傢俱都蓋了一層布,牆上沒有鐘,檯上沒有小飾物或任何餐具,角落裡有一個堆滿了照片和玻璃器皿的紙箱。
「你可以幫我把這箱子放上車子嗎?」
她說,我把箱子提上車,又跑去攙扶她,我攙著她的膀臂慢慢走向停車處,她不斷地謝謝我,我說:「沒什麼,我只是試著善待我的乘客,就像我希望別人善待我母親一樣。」
當我們上了車,她給了我地址,接著又說:「你可以穿越市中心嗎?」
「那可不是捷徑啊!」我很快地回答。
「啊,我不在乎,我並不趕時間,現在我只是搬去救濟院住。」
我看看後視鏡,她的眼睛閃爍著,「我沒有任何親人,醫生說我已經不久於人世了。」
我趕緊把碼表關了,問她:「妳希望我走哪一條路呢?」
接下來的兩個鐘頭,我們在市區內兜來兜去,她告訴我,她曾經在哪一棟樓作過電梯員。
我們也開到她當年新婚時的居所附近,她又要我停在一棟傢俱行的倉庫前,那兒當年是一座她年輕時常去跳舞的大舞廳。
有時她會要我停在某個建築物前,或一個轉角處,在黑暗裡坐著凝視許久,不發一言,當太陽快要升上地平線時,她說:「我累了,我們走吧!」
我們靜默地駛向她給我的地址,那是一座低低的建築物,好像是一個康復之家,汽車道在迴廊之下。
車子一駛近,兩個老人就迎了出來,小心翼翼又緊張地看著她一步步走,他們必定等了她好一陣了。
我打開後車箱,把小箱子提到門口,老婦人已被安排坐在輪椅上。
「我欠你多少?」她打開皮包問我。
「一毛也不欠。」我說
「你必須賺錢維生呢!」「還有其他的顧客呀。」我回答
幾乎毫不思索地,我彎下腰擁抱她一下,她緊緊抱住我:「你給了一個老婦人非常快樂的一段時光。謝謝你!」
黎明的晨光已現,我捏捏她的手就走了。
我身後的門關閉了,同時有一個生命也將進入尾聲。
那夜,我沒有再載其他乘客,我只漫無目的的駕著車」一面落入深沉的思緒裡。
那一整天我幾乎不言不語。
一直想,如果那老婦人遇見一個粗心的或毫無耐心的司機,怎麼辦呢?
如果我拒絕載她兜風,或當時只按一聲喇叭就走了,結果又會怎樣呢?
這一生中也許我再也沒有機會做比這更重要的事了。
人們也許認為人生有周而復始的重要時刻,但其實往往在我們尚未覺察到,甚至別人可能根本不注意時,它卻悄悄而美妙地臨近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