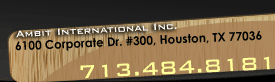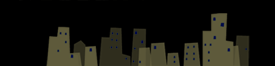推開空碗,拉開座椅,我大剌剌地從餐桌前離開,走出餐廳的剎那,慣常故作輕鬆地丟出一句話:
「我今天白天累慘了!別叫我洗碗。」
餐廳到客廳,要走過一條長長的走道。在行過走道的那幾秒鐘裡,我的心情並不像我的表情般自若,歉疚、心虛夾雜著莫名的委屈。幾年來,在這條短短的走道上,我從未停止過台灣女性的反省與掙扎╴╴傳統與現代觀念在心裡交互爭戰。如果前一天的碗是我洗的,我就安慰自己:
「我又不是完全不負責任,昨天的碗還不是我洗的!」
如果很久沒有洗碗了,我就告訴自己:
「雖然沒有洗碗,飯菜可是我做的,難道不該分工合作嗎?」
如果剛好既沒做飯,又不想洗碗,我就努力說服自己:
「學校的事已經把我搞慘了,累得像個龜孫子!難道家人就不該分憂解勞嗎?否則我結婚幹什麼?又為什麼要生孩子?」
如果久疏家務,我就假裝身體不舒服,露出病懨懨的樣子以逃避疏懶之名。久了,覺得自己行為可恥,就會忽然惱羞成怒起來,叨念著:
「我做了幾十年的家事,憑什麼就該我一直做到死?」
●男女對家事認知有別
家人總弄不懂我為什麼要莫名其妙地生氣,既沒有人指責我偷懶,也沒有人抱怨或推卸洗碗工作。說起來,純粹是我個人腦海裡的天人交戰。像我這樣的女子,自小便被教養著,準備成為一位任勞任怨的家庭主婦,一旦稍稍廢弛了家務,傳統和現代就狠狠地在心裡打了好幾架。而像我這樣經常自責的女人,在台灣的中老年齡層的女性中,絕非個案。
自從五年前,外子自中科院退休後,便陸續接手了一些原本隸屬於我的工作。從那時起,最常聽到外子的抱怨是:
「今天,先是去郵局,再到銀行、市場,接著去八德路買Key Board……整天被這些瑣瑣碎碎的事給絆住,沒辦法做一件正經事。」
我不大確知他所謂的「正經事」指的到底是什麼,不過,在他還沒退休前,那些他所謂的「瑣瑣碎碎的事」,都是我掙扎著在課餘時間包辦,我可從來不認為那是無足輕重的「瑣事」,我總是在晚餐桌上,向他邀功:
「你知道我今天做了多少事嗎?上郵局領稿費、去銀行繳貸款,還去街角修了鞋,到東門市場買了菜,還去超市添購了衛生紙……。」
一位回台開畫展的朋友,在「展前感言」裡,悲壯地寫著他赴美期間強烈的沮喪心情:
「每天扮演著良家婦男,送小孩上下學、煮煮飯、整理花園、種種果樹、除除草……偶爾還會去海邊湖邊釣釣魚,每天晚上望著天空、看看星星、想著故鄉。」
這般詩情畫意、讓女人羨煞、嫉煞的生活,竟被這位男性畫家喪氣地形容為「放逐」!男人和女人對家事的認知真是南轅北轍。也許,男人被社會期待所制約,一向以國計民生為己任,所以,不慣從事看起來沒什麼成就的小事,當他們在做這些事時,便覺得委屈萬分。他們寧可去搶銀行,鬧出點動靜來,也不願在郵局的櫃檯前架起老花眼鏡仔細填寫提款單,因為那樣讓人看起來顯得小頭銳面,不堪重任,台灣的男人一向是被期許成為國之棟樑的。
●新好男人備受感激
我的先生被大家公認是個新好男人。他跟我一樣,勤奮、向上,不辭辛勞。在還沒退休之前,他就是一位肯幫忙作家事的男人。親友來了,看他又切水果、又煮咖啡的,總對他讚譽有加。而我老不服氣,他的朋友來了,我同樣切水果、煮咖啡,外加說笑話娛樂賓客,大夥兒都沒什麼特殊感受,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退休之後,他偶爾在我遲歸之時,接手晚餐,在飯菜端出之際,我總是感激涕零,恨不能以身相許;朋友聽說了,簡直又羨又嫉,把他封為稀有的保育類動物;母親來了,看到女婿在廚房忙進忙出,簡直羞愧地無以復加,屢次提醒我:
「阮一世人不曾讓恁老爸入灶口 (廚房)!哪像汝!」
言下之意,是我「不盡婦道」,而她「教女不嚴」既已成為事實,只好頻頻提醒我該知恩圖報。剛開始,我尚且謹遵教誨,對良人的嘉言懿行致意再三。其後,親戚及來往的朋友不斷地提醒我:
「你哦!運氣真好!嫁了這麼個好丈夫!」
次數多了,越思越想越不是滋味!我不但素性溫良恭儉讓,家裡的活兒幹得也沒比他少,怎麼就沒人稱許我是個好太太?怎麼就沒人提醒他能娶到我有多麼幸運?後來才知道,原來恪盡職守的太太是稀鬆平常,台灣的女人要得到高評價,光憑樂觀、健康、快樂和盡責是不夠格的,她必須堅苦卓絕、忍人所不能忍。君不見每年五月選出的模範母親,評比的標準是甚麼?竟然是痛苦指數!若非吃盡苦頭、歷盡風霜,或正在苦難中煎熬,便休想得到殊榮。最好是家裡食指浩繁,她日夜操勞,使得孩子們出類拔萃,如果家裡正好還有兩位等著她幫忙翻身、包尿片的重度失智老人就更符合標準了。
●跳進「母職神話」的圈套
「在外匯存底高居世界前幾名的社會,如果只用這樣的標準檢視女人,根本是台灣之恥。」
雖然,我常在外頭的演講場合中如此再三陳辭,慷慨激昂地提醒女性不要跳入男性所形塑的「母職神話」圈套裡。然而,回到家,自幼即被耳提面命的「女誡」「女德」總不期然地在內心蠢動撩撥。
年少時,哥哥夜裡餓了,想吃消夜,母親總指使我去幫忙張羅。我若嘟囔著:「他餓,不會自己去弄來吃!為甚麼我就那麼倒楣?」
母親總會生氣地罵道:
「汝這個查某囝仔哪會這尼懶惰!」
哥哥的衣服縐了,「汝幫伊熨一下!」;哥哥的褲子脫線了,「汝幫伊縫一下!」;哥哥的屋子亂了,「汝幫伊整一下!」;哥哥的… …母親嚴厲,我不敢回嘴,但心裡那份愕然及不服氣,幾十年都一直盤據心頭。可是,媽媽振振有辭地說:
「查甫人免學這些,汝是查某,不共款!若無自細漢就學起,將來是要如何持家!」
前年,在紐約見到昔日好友,和她午後款款深談,她提起父母的重男輕女,仍舊久久無法釋懷。她說:
「家裡孩子多,我和弟弟年齡接近,母親儼然當我是保母。我玩晚了,回家一頓好打;弟弟在外玩瘋了遲歸,沒有盡到提醒之責,還是我挨揍。哥哥、弟弟隔幾日各有一個荷包蛋吃,我只有在弟弟心情不錯時,得到恩准舔他盤子上殘存的蛋汁,現在想起來依然心酸。」
我當下忍不住掉下淚來。那樣的殘忍,竟來自相同性別的母親,受苦的女人忘了疼、忘了痛,一轉身即刻成為加害者,啊!女人何苦為難女人!
●女人才是家之棟樑
老人社會逐漸逼近,我們驚訝地發現,輪流由各家兒女照料的老人家求全的並非兒子、女婿。婆婆大駕光臨時,嚴陣以待的,絕對不是她自己的兒子,兒子作息依舊,外出或應酬絲毫不受影響,依然逍遙「家」外;受困的是別人的女兒----媳婦,得像被宣判服刑般地固守、寸步不離地伺候,朋友間例行聚會照例缺席,朋友們都體諒地戲稱她「又服義務役去了」。
台灣的女性想在婚後進修,經常受阻於婆家、丈夫,他們總會說:
「結婚了,還讀甚麼書!把孩子看好就行了,又不缺你賺錢養家。」
可是,男人只要稍稍透露進修意願,卻常常得到絕對的支持,太太總是忙不迭地幫忙蒐集資料、敲打作業。畢業典禮上,很多教授都笑稱學位該頒給隱身男人背後的太太。
我們若有機會到醫院走動,很快便會發現台灣女人才真是家之棟樑。丈夫病了,固然是由太太陪病;婆婆病了,陪病的不是媳婦就是女兒;公公病了,也還是婆婆、媳婦、女兒侍候。如果病的是女人,照顧者依然是女人,女兒、太太、媳婦、媽媽、婆婆……從年少到年老,女人的腳色隨年齡更易,不變的是永遠扮演最辛苦的腳色。前述的陪病,若是女人無力勝任,男人通常也不大伸出援手,他們多半尋求職業看護幫忙。可是,女性如果要求比照辦理,則往往被冠上「不肯盡責」或「偷懶」的汙名。
一直聽說男女平權了!女性對原生家庭也該分擔孝養的重責。我所認識的女性朋友中,多數也都無怨甚至慷慨的扛起,不管已婚或未婚,不管兄弟是否同樣負責,都按月奉上生活費。可是,不管兒子如何不孝,做父母的總還是殷殷告誡女兒:
「雖然民法規定女兒也有繼承權,但是,等我們百年以後,一定要將印章蓋出來,可別真的回來跟你們的兄弟爭產,這會笑掉人家的大牙的。」
電視裡,因為打破蟠龍花瓶而做牛做馬的唐先生,在台灣的家庭裡是絕對少數。男人只要能在下班後,繞道7-11去買些速食解除職業婦女兩面煎熬的困境,就能得到太太甜美的笑靨。然而,這樣讓女人感受溫暖的男人畢竟太少。從《詩經.衛風.氓》裡那位色衰愛弛、哭著被休回娘家的可憐女子開始,一路張望,幾乎都只見到男性的酷烈、女性的辛酸。我們所熟悉的「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的漢魏婦人,〈孔雀東南飛〉裡被婆婆欺負的焦仲卿妻劉氏、被丈夫戲弄的秋胡妻子、苦守寒窯的王寶釧、受辱的焦桂英、被棄的秦香蓮、趙五娘,還有怒沉百寶箱的杜十娘……,哪一個不是歷經折磨!甚至現代的琦君、潘人木、蕭麗紅的作品裡,都還充斥著堅毅隱忍、含辛茹苦的女性,難得看到一位不甘雌伏、意欲享受生命滋味的芸娘,卻也無法擺脫傳統女性痛苦的宿命。父權社會裡,將「苦難」賦予崇高的光環,緊緊箍住女人撲撲欲動的情思。
●前衛書寫不敵真實人生
中國文學中的女性書寫,一逕延續著「怨」的傳統,時代的巨輪像踩著風火輪般快速轟轟往前跑,實際人生中的台灣女人,卻用被傳統裹著的小腳碎步追趕,怎麼不累得頻頻原地喘息!李昂塑造了一位殺夫的女人,雖然聲音瘖啞、怒吼窒悶,總算讓女人從隱忍的「怨」匍伏前進至不平則鳴的「怒」來。然而,前衛的書寫不敵真實的人生,《殺夫》出版後的多年,曾應台北市文化局之邀,前去擔任母親節徵文比賽的評審工作,印象最深刻的,便是前來應徵的一千多篇文章裡的母親,幾乎個個身世坎坷,人人一把辛酸淚,卻悉數「無怨無尤」!這不是神話,而是真實發生在二十世紀台灣的事,我們不停地頌揚「吃苦」的美德,卻忘了只有主中饋的女性快樂了,家庭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幸福,由怨而怒,女性情感發展史一路蜿蜒迤邐,何時才能敞開胸懷,理直氣壯地享受「快樂」?
屬於我母親的年代,女人成天在廚房裡接受煙燻火燎、和煤球奮戰;屬於我們的年代,許多的女人希冀在廚房之外找到自己的天空,卻仍不免縛手縛腳、步履癲狂;多麼希望我們的下一代的女人能享有更多的平等對待,女性能徹底在思想上得到解放,體認到:
「享受生命是權利,不是奢侈,毋須愧疚;兩性共組的家庭,男人分擔家務是理所當然,只需給予尊敬,女人不必感激涕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