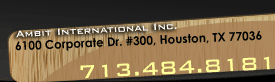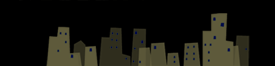十五歲那年冬天,母親因為疲勞過度而過世。半個月後,我見到了在母親嘴裡詛咒了六年的父親,並隨他回到闊別已久的小鎮。走在已有些陌生的父親背後,我的心裡充滿了怨恨與恐懼。
也許是為了彌補些什麼,父親努力地盡著一個父親的責任。可是這一切都無法消除六年來他加給我和母親的傷害。六年前,為了圓滿他的「愛情」,他遺棄了我和母親。從此我們開始了異鄉的漂泊,並讓我永遠地失去了生性要強的母親。
每天我努力讀書,不和父親多說一句話。我知道,只有考上大學離開小鎮,才是我走出這個可憎的家最好的捷徑。仰仗著一張張獎狀,我變著法子詐他的錢。我要替母親索回六年來他欠下的一切。
高考前的家長會上,班主任告訴父親,我是最有希望考進名校的一位。父親瘦黑的臉上第一次有了孩子般的笑容。
那年的八月十三日,我收到了全校第一份錄取通知書,上面赫然寫著一所航海學院的名字。父親驚呆了,木木地楞在那裡,我心裡卻有一種痛擊對手後的快意。從此我就可以堂而皇之地遠離這個家,到大海上過浪跡天涯的生活了。
開學前,父親執意要送我去遠在大連的學校。
報到的前一天,我們住在一家廉價的小旅店裡。清早起床,父親正捏了枚刀片在鏡子前刮鬍子。因為用力不均,他瘦黑的臉上留下了幾道或深或淺的刮痕,紅紅的將要流血的樣子。
我的心一下就酸了起來,忍不住說道:「待會兒再刮吧,我到樓下買把剃刀架。」父親轉過臉來,有些受寵若驚地看著我,良久才眼眶泛紅地說:「家裡有的,買了只用這一次,太浪費了。」我突然想哭,我知道父親是心疼錢。一年前父親因病退休後,日子一直都過得很艱難。我低著頭快步走出浴室,不願父親看見自己眼裡噙著的淚水。
旅館裡的那段親密並沒維繫多久。父親回到小鎮後,我們的感情又疏遠起來,和從前一樣淡漠。
四年後,我畢業了。從此開始了大海上漂泊的生涯。走的那天,父親到車站送我,同行的還有伯父和幾位朋友。伯父低聲安慰父親:「又不是不回來,別這樣板著臉,讓人看笑話……」伯父還沒說完,父親突然就哭了,在人潮洶湧的站台上。我的心倏地酸痛起來。
我知道一向堅毅的父親為什麼把持不住。幾天前,報紙長篇累牘地報導著一則消息:「香港『長勝』號貨輪遭海盜劫持,二十八名船員沈屍海底。」望著父親微白的雙鬢和肆無忌憚的淚水,我想說些什麼寬慰他,可剛一張口淚水也簌簌地流下來……
半年多寂寞的航海生活漸漸磨去我年少的輕狂。船到香港時,我給家裡打了出海後的第一通電話。妹妹告訴我,我走後父親的身體一直都很不好,幾天前父親刮鬍子時,手直抖把臉都刮破了,流了不少的血。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熱了,淚眼迷濛中我彷彿又看見幾年前旅館裡父親臉上那一道道滲著血漬的刮痕……
掛斷電話,我徒步跑出港區,給父親買了一支電動剃鬍刀,包裹寄回。我在包裹右下角空白的地方細細地寫了一行「爸爸,我愛你」。
四個月後,我接到了父親病危住進醫院的電報。
當我從遙遠的美國飛回家中時,昔日身材魁梧的父親已靜靜地睡在一只狹小的骨灰盒裡了。父親供桌的玻璃下,工工整整地壓著包裹盒上剪下的那行「爸爸,我愛你」的留言。
伯父默然地望了我很久,才哽咽地說:「你爸走時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每次父親經過急救後,醒來總要胡亂地說許多很混沌的話,卻一遍遍清晰地喊出我的小名。
在最後的那些日子裡,父親最大的快樂就是用我為他買的那把剃鬍刀貼一貼早已刮得乾乾淨淨的臉頰。父親時常和伯父提起那把剃鬍刀,說是那次在洗漱間暈倒時摔得掉了瓣,竟沒一點事兒,只怕是用到死也壞不了了……
撫著剃鬍刀黑亮的手柄上頭的刮痕,我的淚禁不住又簌簌地流下來。這些年來,自己的偏執與冷漠不知在他心底留下多少的傷痕。
父親故去已三年了。每年父親的忌日,我總要拿出那把剃鬍刀,充足電,然後必恭必敬地放在父親的遺像前。我只願有天它又能在父親的手裡「吱吱」地刮起來,替我吻一吻父親那一臉的滄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