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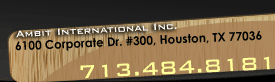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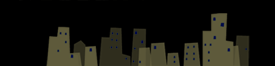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me >> 文摘 >> 舒香滿婷 | |
 | |
| 我的文字我的歌 文/舒婷 | |
那天你問我:「妳唱歌到底是唱給誰聽呢?」 似乎是第一次有人對我提出這個問題。嗯,唱給誰聽啊?耐人尋味的不是我倒底該怎麼回答你,而是你所發表的這個非常有趣的念頭。 我好像從小就愛唱歌。 話說我兩歲半那年有一次高燒不止,爸爸抱著我急著找醫生,在家附近的那個後來被爸爸稱為蒙古大夫的傻醫生,說什麼把整個診所的冰塊都搬出來舖在我身上還退不了燒,幾乎被宣判醫救無效,最後送到三總找當時還是小兒科住院醫師的表姐夫求救。當三總的主治大夫向爸媽問診時提到,這個小女孩有沒有精神不濟或食惑不佳的情況時,媽媽的回答是: 「不會啊!昨天她姐姐生日,她還唱生日快樂歌唱得很大聲,還大口吃蛋糕咧!」 不曉得是不是發燒時吃下去的東西口感不好,我至此對甜食沒有太大的偏好,但開口唱歌,成為我與說話並重的另一項主要使用聲帶的效果。 我記得小時候媽媽要為我們的唱歌說話留下紀錄,家裡還沒有那種直立式的錄音機,更別提音響或麥克風了。我們家的那台第一代錄音機的外型和大小長得有點像VHS錄影帶的迴帶機(不過現在小孩可能連迴帶機是什麼也都不知道了,他們只曉得DVD吧!),是長方型平躺的那種規格,要放取錄音帶的時候那個透明的蓋子是很快地迅速向上彈開,收音的地方是一個小小的孔在按鍵的旁邊,錄音時必須同時用力按兩個鍵,而且要兩隻手一起喔!不然力氣不夠大。整台機器只有六個按鈕,在我那個年紀看來是非常複雜。 我還保留著很小時候唱歌的錄音帶。那時候很風糜最家喻戶曉的一齣電視連續劇是「包青天」,每天晚上八點一到,家家戶戶的客廳都響起「開封有郭(個)包青天,鐵面無私辨忠奸,江湖豪傑來相見,王朝和馬漢在∼身∼邊∼」的這首主題歌。 在我幼稚園的時候,我生平灌錄的第一首歌就是「包青天」,第二首歌才是「茉莉花」,而且還自己加上配樂和間奏喔!其實我小時候是個黃毛丫頭加破鑼嗓子,聲音非常好認,最啞的那個就是我,所以和姐姐合唱時完全可以知道誰在搶戲。當媽媽按下錄音鍵,小小聲地一說開始唱,我和姐姐就開始吼了: 「開封有郭(個)、包青天,鐵面無私、辨忠奸 「噹啷噹啷噹啷噹、噹啷 「江湖豪傑、來相見,王朝和馬漢在∼身∼邊吔∼」 然後中間什麼鼠怎麼翻什麼鼠怎麼滾我們是有模有樣地胡亂混唱一氣,但是節拍和段落還是精準的,最後來一句 「這五鼠∼義、結、金、蘭嗯啊∼ 「七俠和五義,流、傳、在、民、間A∼ 「ㄉㄨㄤ∼…」 這卷錄音帶我猜已經失傳了,有心人士若有拾獲,麻煩請上架eBao標售。注意,是eBao而不是eBay喔!本人及本家族一定出高價收購,絕不食言。 除了民歌之外,我是聽流行音樂長大的。第一首喚醒我的流行歌曲,是潘越雲繼「天天天藍」之後的「再見離別」。因為媽媽上班的時間比較早,在準備出門前她會打開音響收聽廣播,在七點中廣新聞前的最後三分鐘廣告,我會聽見張小燕的聲音說: 你說離別容易,再見難;而我說再見容易,離別難。聽潘越雲的歌聲─「再見離別」。 那年我可能十歲不到,潘越雲歌聲裡的憂鬱我不能意會,想不懂的是,再見和離別有什麼不同呢?為什麼要分誰比較難? 從玉女偶像歌手的糜糜之音以降,羅大佑和丘丘是當時樂壇的另一股勢力。我們唱的是羅大佑的「鹿港小鎮」和「戀曲1980」,男生女生出去玩的時候唱的是丘丘的「就在今夜」和「河堤上的傻瓜」。那個時候的流行歌曲詞美弦合,意境單純又不失華麗,造就了不少真正的歌手。可惜有些人在商業主流的導向下,對音樂的執著投入了另類催化,幸虧多年後羅大佑和娃娃合作了「四季」專輯,才讓我確定當年他們曾經的存在地位,「如今才是唯一」找回了我對那個時期的依戀。 港劇的入侵引起了一波港星和廣東歌的潮流,我國中的那幾年聽得唱得幾乎是武俠劇的主題配樂。已故羅文和現在還在開演唱會的甄妮搭檔唱出的「射雕」系列,我敢說在當時的中學生沒有不知道的。諸如「世間始終你好」、「兩忘煙水裡」還有「桃花開」、「滿江紅」等等…,在推行國語的那個年代,我都覺得我的廣東話聽力好像比台語更好。但隨著翁美玲的自殺消香玉殞,我就不再看港劇了。 後來的幾年幾乎是電視劇和電影的天下,任何歌曲只要搭上電視片頭片尾曲或有個什麼電影原聲帶收錄的話,肯定天天打日日播,疲勞轟炸下不紅也不行。羅大佑還是位居樂壇教父,李宗盛從「木吉他」蛻變後竄紅,成為音樂製作第一把交椅。我聽的是三毛的第十五號作品「回聲」,在三毛柔細且輕膩的旁白下,聽齊豫和潘越雲娓娓詮釋一首首的「曉夢蝴蝶」、「七點鐘」、「遠方」和「夢田」,你會真的隨三毛遠奔撒哈拉,隨她帶著你去沒有人能告訴你到底有多遠的遠方。作家和歌手的結合,這算是先趨,最近幾年張曼娟和張清芳的作品,就是最佳的仿傚吧! 王新蓮和鄭華娟的出現,就像現在「無印良品」的光良和品冠一樣,是同時期的另一對創作組合。她們的「往天涯的盡頭單飛」,沒有女孩間的濃稠黏密,反而像男孩子的海闊天空。一首「啦啦歌」,從頭啦∼到尾,弦律輕巧,合聲多重,難度頗高。後來我才知道,王新蓮的「風中的早晨」其實比「再見離別」更早左右我的音樂癖好,她後來的單飛之作─「不要太多」,歌詞蘊含的意念到現在仍舊是我追尋的;鄭華娟的產量亦不遑多讓,包括「天堂」、「謝謝你曾經愛過我」、「加州陽光」這些到目前為止我上卡拉OK都還會點唱的精典。 歌曲對於我是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的迴響,每一首我能告訴你的歌曲,都有我那時的酸楚或甜蜜,我可以很明確的指出那一首歌曲的年份和當時的事件,因為我的歲月和那首歌在當時相互依存著。我有全部的潘越雲和陳淑樺,就為了不讓自己忘記「生別離」和「像我這樣的單身女子」。 高二的那一年,是陳淑樺的「夢醒時分」讓我落淚;考大學的那個暑假,黃品源的「你怎麼捨得我難過」在我打工的麥當勞熱力放送;大一的時候,「優客李林」的「認錯」是我們在社團辦公室的必選挑戰歌單。從那個時候起,在唱別人和自己心情的同時,我的蝌蚪字也開始在社辦的「靈弦天線」裡爬出了自己的靈弦心情。 後來的十年,我用歌和文字記錄自己的每個轉折,我也用歌和文字傾訴自己的每個起伏,週遭的人更透過我每每的歌和文字覺察我的處境。 所以當你問我:「妳唱歌到底是唱給誰聽呢?」 我很難理直氣壯地告訴你一個想當然爾的答案,因為,那個人和那個對象不是具體的。就像現在在看這段文字的你一樣,都是個抽象的接收。 一個完美的演出,是要天時、地利、人合的。我要對我選的歌有感覺,在唱的當下有情緒,聽眾也付出適時的共鳴。最重要的,是演出本身的爆發力能不能把這三者串聯,讓目光聚焦。 是寄情歌曲的結構,是抒發蟄伏的情感,是感動共有的曾經。 我的文字就跟我唱的歌一樣,是一種寄託,是一種發洩,是一種互動。 幾個月前我回台灣的時候,和一個同時也靠寫作為「生」的朋友談起我們血淚交織的創作路。我所謂的「生」不是靠寫作吃飯,是仰賴寫作讓自己的生命有一個理由去延續。靠寫作來反省自己,靠寫作來回饋自己,也靠寫作來磨練自己。我提到我的電腦裡大概有幾十篇未完成的文章,每一篇都是在有情緒有感覺的時候起的頭,但因為沒有一股作氣不然就是靈感不足以支持意念而都未竟完成。最遠還能追溯到2000年的雪梨奧運,我電腦都不知道換了幾台了,這些有頭無尾的孤兒就被我不斷搬來搬去。這樣的落魄引來他的一番嘲笑,因為我還曾經試圖想偷懶把兩三篇類似意境的未完成拼成一頁大雜燴,結果當然是自己都覺得慚愧。 搞了半天,你這麼一個簡單的問題,我居然要從三十年前發高燒的那天開始解答,現在大概也只有你有這個能耐讓我如此大費周章,賣弄唇舌。 有人願意聽我唱的歌,因為我是在唱自己,不是在模仿任何人。我的投入和熱情透過我口中的歌曲傳遞出來,如果聽的人心有慽慽,我這個唱的人也與有榮焉。就像我隨手的這些小故事,是在寫我自己,不是在為人作嫁。我的付出和真誠從我的彈指間流洩,雖然你看到的不再是我爬在「靈弦天線」上那獨特的蝌蚪字,但只要還有一個人能從我的字列間找回自己的一點點過往,我都會為了他和自己繼續寫下去。 我想找的是當年的黃鶯鶯和蘇芮,我想等的是當年的吳楚楚和陳志遠,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另一首「浮雲遊子」或是「野百合也有春天」。就像我不清楚在那麼多的文字城堡裡,到底自己在尋找的是「擊攘歌」裡的小蝦學姐,還是殷切期盼另外一個朱天心的誕生。 不知道這樣的答覆,是不是能滿足你的疑惑和排斥。 我是第一次思考這個問題,因為我從沒真正想過「為什麼」。能唱能寫是父母給我的禮物,但喜歡和持續地去做又是另一回事。我猜這是一種享受吧!就像花時間去做一道工夫菜對我而言也是一種陶醉,讓我的吃客們食指大動,把一桌好菜吃乾抹淨帶給我的是一種分享,也是一種獲得。 這就是我唱歌的理由,是為別人,也為自己;不需要什麼特別的場合,也不會去規避什麼特別的場合;不見得要知道聽眾是誰,也從沒有去挑選聽眾。 下一次,我唱歌時,你可以仔細品味我的噴張悸動嗎? 下一次,我寫字時,你可以深刻體會我的蛻變成長嗎? 如果你可以的話,一定要告訴我,讓我有更多的理由去繼續這賴以為「生」的樂趣。 (寫在民歌三十紀念演唱會前夕) 再見離別 不要太多 生別離 像我這樣的單身女子 | |
| [ 評論此篇文章 ] : [ 轉寄 ] : [ 列印 ] | |
| This page has been view 4052 times | |
|
| |
|
城市電通
| |
|
Home | About
eBao | Events |
Member Suppor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