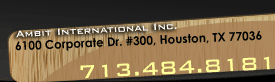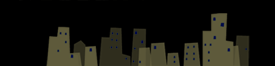「向前、向前。直直的往前去。別害怕!不要往下看,更不要回頭望。對了,看著前面,就是這樣,就是這樣…」父親的聲音在耳背後漸行漸遠,他的聲音愈模糊我的腳步就愈加急促,直到我人仰馬翻的摔倒在地時,才知道已經學會獨自上路了。不再需要像棵青菜一樣的被母親擺在車籃裡,不再需要躲在爺爺的背後還得要抓著他鼓鼓的肚皮。擺脫束縛乘風飛翔,世界就在腳底下,風景就在前方。正滲著血的皮肉之痛豈能掩蓋內心的歡愉,和我一起跌坐在地上空轉的車輪也嘎-嘎-嘎地笑了…。
二○○四年一月十八日,凌晨,三點零五分。
皎白的上弦月不知何時早已爬過牆頭高掛夜空,它嘴角邊默然竊笑的弧度是偷窺了我童年的心事?還是早已預言了這場浩劫,回望我以悲憫的容顏?蒼白月色下,五十八本編寫著不同年份的相簿散落一地。1986、1990、1997、2001…,一本本精裝厚實的相簿宛如一具具華麗的棺柩。我像個半夜持斧掘墳的人,拼命地敲繫著記憶的傷口,俯視封塵往事如驗屍般的心情沈重而心虛。我一頁頁的打開它,盯著相簿裡的影中人邊翻邊抽、邊翻邊抽……滑動的指尖在層層疊疊歲月裡急速穿越,唯恐稍一停格所有的畫面便要奪框而出。
「天啊!這麼多相片。妳在做什麼?」芸走進屋裡,剛下班滿臉疲憊的她,看到我坐在滿坑滿谷的相簿堆裡,驚訝的問著。
「你說離婚的人是如何處理他們的相片?燒掉?撕掉?還是扔掉?」我埋著頭,專注的翻著相簿。
「所以,你要…」她坐到我身旁,撿了張丟在地上的照片。
「抽出來的部份是他的,難不成我還要帶著他走?而留在相簿裡的全是我和孩子的回憶,送給他,他會要嗎?說不定哪一天全給扔到垃圾桶了。他……那個瘋子。」我看著她,思緒卻飄向遠方。
「妳今天又哭了,是不是?」她嘆口氣瞪了我一眼,繼續說。
「妳這是何苦,像我就什麼都沒有,什麼也沒來得及帶。唉!有時想想,人有回憶只是徒增痛苦煩惱罷了!不是燒掉、撕掉、或是扔掉,是忘掉。忘─掉,OK?」她語氣堅定的看著我。
「可是,你至少擁有孩子,而我卻全給了他,你知道孩子是我的命…」
「好啊!去要回來。自己想辦法過日子,妳可以嗎?記住,妳是他們的媽就永遠是他們的媽,就像他們永遠只有一個爸爸一樣,等孩子大了自然明暸。走到這種地步只能往前看,勇敢一點。」她見我又眼眶泛紅,遂轉移話題。
「早上我忘了告訢你,冰箱裡有煮好的紅燒魚,還醃了些你愛吃的泡菜。電鍋裡有飯有梅干扣肉,不要客氣把這裡當作自已的家,你得要照顧好自己的身體。還有,如果你再哭,保證眼睛瞎掉。早一點睡吧!」她起身走回她的房間,我望著比自己還瘦弱的背影,淚還是忍不住的滴了下來……。
芸與我曾是工作上的伙伴,在我不需要為五斗米折腰的少婦歲月,她已經是個獨挑生活重擔的單親媽媽了。幾年下來,不管是工作上的挫折亦或是情感上的牽動,她始終泰然以對。我無法了解支撐她力量的信念來自何方?但她卻是永遠第一個可以給我鼓勵的人。
於是,這一間原本要分租出去的一房一衛浴,竟成了我的避難所。當外面的世界,雷聲大作風雨交加無情的鞭撻我時,這一間12X10的微小空間給我一個家所有的溫暖。在崎嶇的情感道路上,我們因際遇相同有緣聚首,相濡以沫而相互扶持。那些恨過、愛過、怨過。失落的、擁有的、過去的、還有未來的……似乎所有的故事都在這小屋裡有了新的詮釋。儘管友誼的溫度根本無法掩蓋午夜夢迴時的思子情切,但在那樣冷凜的冬日,確是我唯一可以取暖的方式。
我在哪裡?到底在哪裡?哦!我的家。我的孩子呢?我的身體向前衝,但是腳步卻往回走。然後用跑的,拼命地跑、蒼惶失措地大叫:孩子、孩子…我的孩子呢?….。突然,「碰!」一聲巨響,我在身體即刻裂撕的顫悚中驚醒。黑暗中我安撫著猛然懼動的心跳告訴自己:是個夢,只是一個惡夢。不怕,不怕,這裡是安全的,這才是我的家。我還活著,我要活著!可是,孩子呢?我的孩子啊─如此重覆的景像總在夢境中揮之不去。幽暗夜色裡,淚靜靜的滑過臉頰沾濕被褥,在滉惚光影中漸次熟悉這原本陌生的角落,一個可以讓我哭泣的肩膀。
然而,一個逃家的女人,有悲傷的權力嗎?掙脫情愛桎梏,解放痛苦婚姻的意識,是否就像小時侯追逐自由的狂熱一樣?是否也像眼前這五十八本相簿,無怨無悔地記錄了一場悲劇的進行曲?那演戲的人癡傻,看戲的人更加瘋狂,悲喜人生盡是浮光掠影的印記罷了。此刻即將落幕,燈光熄滅後我要親手為你拉下布簾。「唰─唰─唰」。忽地,一張相片不經意地自相簿中輕輕滑出…。
相片是兒子的騎士風姿,腳踏車是GarageSale討價還價後以十五元買來的二手車。六歲的他戴著頭盔,手腳護套全副武裝,被我裹得像個不倒翁似的在公寓前的車道上,來回穿梭展現雄風,惹得只能坐在三輪車裡三歲的妹妹既羨又妒。照片上的日期:12.11.1994.
黑夜過去,天色漸漸泛白。我將照片握在掌心放到胸口,彷彿又聽到父親的聲音:「向前,向前。直直的往向前去,別害怕,不要回頭望……」他的聲音很遙遠,很遙遠,但卻字字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