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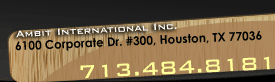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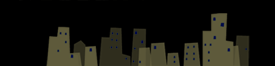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me >> 文摘 >> 舒香滿婷 | |
 | |
| 「John, Did You See John?」 文/舒婷 | |
許多年前,我剛開始這份工作的時候,我的辦公室裡只有我一個女生,當然,現在還是一樣。不過在那時候,除了五個和我年紀差不多的男生之外,我們同一間辦公室裡還坐著另外兩位老先生,巧合的是,他們兩位都叫「John」。 其中一位年紀較大,行動也比較不方便,因為他的右腿開過刀,走路需要拄著拐杖,我猜他應該有六十多將近七十歲吧!我不知道他早上都幾點來上班,肯定是很早,到了下午五點,他是準時下班的那種老先生。他的桌子總是收拾得很乾淨,他在這行的經驗豐富,幾乎是幹過所有的職務,所以他的工作是風險管理與評估。每當你問他任何問題,他的開場白一定是:一九幾幾年的時候,我在某家公司任職某某職務,當時的作法是如何如何…。 這位左腳John是個脾氣超好的老先生,講話不急不徐,而且非常樂於助人。當然,難免有時候,你會嫌他這位老人家有些囉唆,因為他一旦打開話匣子就停不下來,再加上他豐富的人生閱歷,他總是可以輕易地把所有的事都連在一起然後告訴你一個很長的故事,如果你有時間的話當然是很好,不過通常話題的開始都只是在走廊上碰到的一個簡單問候而已,然後你就需要一步一步越走越遠直到你聽不到他的聲音才能結束。 另一位年紀沒那麼大的John就不是這樣了。他的個性很急,說話很快,好像隨時都靜不下來,他在總務部門工作,管理公司內所有和設備有關的事務,舉凡電話、冷氣、桌椅、影印機都在他的管轄範圍,他的桌上永遠都堆放一疊疊的資料,電話響個不停。全公司所有人都認得他,因為你一進公司第一件事就是要申請一個分機和門卡,他就是那個負責設定和發放的人。 這個性急John的脾氣就是快,他除了坐下來的時間之外都是在小跑步,就算是從他的坐位到印表機拿張紙都是用競走的,而且他會邊走路邊說話,剛開始我都誤以為他在和我說話,因為我就坐在印表機前面,久了我才發現,那是他自我溝通的一種方式。如果從他說話的口氣和內容來解讀他當時的情緒的話,你會錯認他隨時都處於激動的狀態,其實,那只是他的個性和表達方式而已。 這兩位John很有趣,一個動一個靜,一個快一個慢。其中一位是一天上班八小時除了吃飯以外可能有七個半小時都在座位上從事他的分析工作,另外一位是一天上班八小時除了吃飯以外可能只有半個小時在座位上回覆電話和聯絡事項。事實上,他們每天的交集就是中午用餐的那一個小時。 那時候,這兩位John是報告給同一個老闆,那是一位優雅的英國女士。她的個子不高,舉止從容,每天到了他們的午餐時間,大約十一點半的時候,她會從我辦公室的前門進來,對著我的後方說: 「John, Did you see John?」 她沒有頭腦不清,我們也絕對不會搞混她是在問誰話。因為一個John永遠都坐在那兒,一個John通常都在亂跑。 我在這樣的情境下工作了兩年,我們同一間辦公室的六個年輕人和兩位老人家是相安無事、相敬如賓,偶爾從後面傳來他們說話的聲音,我就當是他們在自言自語。一來呢,是因為有時他們講的東西我實在聽不懂;再來呢,是我怕一起頭就沒完沒了,無法控制結束交談的時間。所以,在這兩年內,我和他們標準的對話都是些問候語,像是「早安」或「再見」之類的,了不起多加兩句「您週末過得如何?」不然就是「您中午吃些什麼?」一些不著邊際的應酬話。 因為左腳John的行動不便,性急John便成了他的代步者。他為他去印表機拿報告時就順便為我們大家拿;他幫他去郵件室取信時就連同我們大家的全都抱回來發一發;碰到下雨天,他會替他撐傘開門護送他去開車回家;倒咖啡時,也一定會多盛一杯給他。其實我沒有注意過他們的這種共生方式,有時反而還覺得,面對茫然或無法結束的對話,真的無奈又浪費時間。 這樣的情況一直到左腳John退休,公司為他舉辦了一場隆重的退休儀式。他們的英國女老闆很熱心地籌畫,大家還集資買了一台精巧的數位攝影機送給他做紀念,公司的大頭們幾乎全都到齊了,但是那時性急John正好在休假,所以缺席了。不知道是他不想面對這種分離的場合呢?還是他真的早就安排好旅遊的行程。 左腳John退休後,他的業務被轉移到另一個部門去處理,因此,他的座位便空了出來,我們也一直還不需要找人去替捕那個位置,久而久之,那個隔間被我們拿來堆東西。 有淘汰準備捐掉的電腦、有一箱一箱一大堆亂七八糟的不同的電線、有暫時不用卻沒地方塞的檔案架,有時候,我們還把早餐或是一些吃的東西放在那兒讓大家走過去時就可以拿一塊來吃,反正弄得很亂就是了,說實在的,大家也並不搞得很清楚到底那裡真正堆放著什麼。 偶爾,我們會聽到那個英國女人提到今天和性急John一起約了左腳John吃午飯,那也是不關我們的事,你知道的,我們年輕人總是和他們不同掛。 左腳John退休後的一年,性急John的身體出了狀況。 他開始請長假,我的辦公室和整個公司陷入了一片小小的混亂。 一向由他負責管理的事務一下子沒人嗆聲,大家都在設法幫忙找答案。從那些各個辦公室的安全警報裝置、到裝潢隔間或屋頂漏水,就算是那個我們以為很簡單的電話系統,都沒人能一次搞定。運氣好的話,大家集思廣益翻箱倒櫃可能可以找到一點蛛絲馬跡;運氣不好的話,打電話給John也接不到他的手上,只能請有需要的人耐心等待。這些公事,慢慢的,一步步被我們消化,他的辦公桌被他的英國女老闆收拾得整齊規律,只是有一次我去洗手間竟然發現她在裡頭接手機,因為所有的人開始只能直接找她接洽。 對大部分的我們來說,日子還是一樣的過,性急John的休假對安份守己的老百姓而言沒有構成大礙,我們甚至還覺得,反正事情一定會有人繼續做下去的嘛!沒什麼大不了。 然後有一天,公司負責郵件發送的黑人大哥提著一個郵箱到我們辦公室,把郵件一一發給我們,我正覺得納悶:好多天都沒郵件,可是應該有人要送報告給我啊?我問黑大哥:怎麼這麼好,今天你大駕光臨送到我們辦公室來?黑大哥說:因為郵件室裡屬於你們這個辦公室的格子早就擠爆,再也塞不進任何東西了,我只好直接拿過來,順便提醒你們─John不在,你們還是要記得去拿郵件,萬一有什麼重要事擔擱了就不太好。 是喔!我們這幾個少年吔誰在拿郵件啊? 一個多月後,性急John還是沒回來上班,而且辦理了離職手續,因為他嚴重的躁鬱症被醫師勒令必須在家休養,他因此結束了與我們公司長達十餘年的勞資關係,也或許,就此結束了他的職場生涯。 性急John沒有小孩,我對他的家庭狀況瞭解不多,只陸續從一位同事口中知道他過得還可以,病情持續控制著,但公司大部份的人都再也沒有見過他,包括他的英國女老闆在內。我不知道我們該不該關心他,不過還是會經常聽到他的名字,因為實在有太多瑣碎雜事歸他管,無論你願不願意,從前你都得找他,他也都能解決,而現在,大家提到他都是跟著一大堆從前與他共事的經驗,然後去從破碎的記憶裡來發掘推測他可能的解決方法,那不見得會對,因為從前我們從來不想去學,也不用去學,只要一通電話給他就好了。 在七月的第一個長週末,美國的國慶日,我從外地渡假回來,上班後聽到的第一個消息就是:性急John過世了。 他走得很倉促,似乎是飲酒過量導致心臟病發,在送醫途中不治逝世。當時沒有家人在身邊,醫院通知了唯一與他還有聯繫的那位公司同事前往處理後事。 我從前曾經聽過一項統計,在慶典或節日的時候是自殺的高峰期,尤其對患有憂鬱症的病人而言那是他們的難關。因為大家都在愉快玩樂,瘋狂慶祝,他們可能更覺孤單寂寞,他們可能更覺傷心難過,很容易在沒有陪伴的情況下而想不開。 誰也沒有想到他會這樣就走了,我也不相信他是自殺,我知道他不是酗酒的人,可能只是單純的一時飲酒過量。而令人玩味的是,他在事發的當天早上還打電話給那位與他交好的同事,他們像以往一樣聞聊了幾句,一切都很正常,不像是厭世準備輕生的口氣,但也有可能,他想在最後的時間和最關心他的人道別。 自性急John過世後,每一天我們都在打聽告別式的時間,令人訝異的是,他的家人似乎沒有打算要為他舉行任何儀式,在這種情況下,他辭世前最後一位電話聯繫的同事便義不容辭地一肩扛下這項任務。 從蒐集照片、生平,到聯絡教堂、申請骨灰,全部由這位才剛過二十六歲生日的小伙子包辦。他似乎是想獨自為這位老友完美地規畫他生命中的最後一場演出,我們要幫忙,他說他一個人還行,我們想捐錢,他說把支票開給教堂就好了。可是直到告別式的前一天,我們還為找不到一張像樣的照片發愁,手上有的,是人事部提供十餘年前他剛進公司時的檔案照,當時他留著鬍子,看起來比現在還老;再來,就是駕照上的一小方格照片,看起來也怪怪的。於是,我們開始找尋公司這三年來所有的活動照片,看是否能幸運地讓我們看到任何一個他的笑容,可惜,不是只有側面就是距離太遠,無疾而終。 告別式那天傍晚,性急John的家人還是沒有現身,但是左腳John來了,拖著前一天才又動手術打鋼釘的右腿,左腳John扶著他的拐杖,西裝畢挺,七點不到就坐在第一排,看著那兩張照片裡他的老友,也曾經是他藉以代步的右腿,臉上的表情窺探不到他的心情。 當牧師念著同事所撰性急John的生平事蹟時,我才發現,我和性急John同一個辦公室那麼久,竟然對他的瞭解那麼表面。他出生加州舊金山,在德州達拉斯就學;他打過越戰,還是紫勳胸章退役;他酷愛釣魚,是德州一個很權威的釣魚協會榮譽會員;他喜歡貓,他身後留下好多貓待人認養;他和他的太太非常恩愛,雖然他們沒有小孩,我還以為他們處於分開的狀態。我對他的認識,充其量不過是位專業水電裝潢工,性格急躁,為人低調。如果他不是我的同事,他就像任何一個我在逛街時根本不會注意到的德州佬一樣,平凡,普通。 我很遺憾沒有機會能再多親自瞭解性急John一些。看著陳列在講桌邊他遺留下來的釣具,配上我們僅能找到的他那兩張照片,我無法拚湊出他戴著棒球帽、頂著烈陽、手持釣竿、一個人無聲地坐在小板凳上啜飲啤酒的海邊是什麼模樣。嗯,我真的想像不到。 會後,我擁抱著久違的左腳John,望著另一邊他們那位優雅的英國女主管,耳邊竟然響起遙遠又嘹亮的那句: 「John, Did You See John?」 | |
| [ 評論此篇文章 ] : [ 轉寄 ] : [ 列印 ] | |
| This page has been view 4016 times | |
|
| |
|
城市電通
| |
|
Home | About
eBao | Events |
Member Support | |